追寻父辈的精神长河
- 外汇
- 1小时之前
0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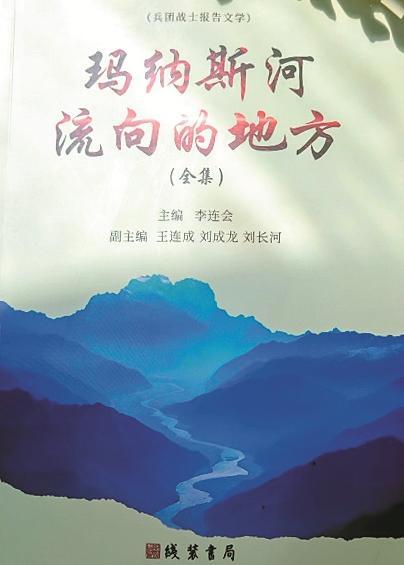
●孙玲
玛纳斯河流向哪儿?它流向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六师五家渠市。六师五家渠市下辖14个农牧团场,其中的新湖农场,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有父辈的青春热血和奋斗岁月,有我难忘的童年。
当我翻开李连会老师主编的长篇报告文学《玛纳斯河流向的地方》,指尖触碰到的不只是纸页的粗粝,更是戈壁滩上被烈日灼烤过的碱土,是父辈们年轻手掌上磨破又结痂的血泡与老茧。玛纳斯河,这条在地图上蜿蜒的蓝色曲线,瞬间奔涌成一条时光之河。
这本书带领我们追寻的,是老一辈兵团人用青春、汗水乃至血肉,在新湖农场以及石河子等地的亘古荒原上刻下的沉重足迹;我们感受到的,是那段激情与苦难交织、理想与乡愁缠绕的峥嵘岁月。书页间流淌的,不是冰冷的历史陈述,而是父辈们依然滚烫的生命余温,是时代车轮碾过荒原时,那一声声刻骨铭心的回响。
我,一个喝着天山雪水长大的兵团子女,此刻正跟随这些质朴的文字记忆溯流而上,向着生命源头进行一场精神的跋涉。
书中张怀礼老人的老家在山东省安丘县(现安丘市)。他参加过1948年的济南战役,当年是一名机枪手,复员后于1965年支边来到新湖农场。张怀礼老人的回忆里,有好几个环境描写的片段让我沉醉,那都是我小时候看到过的景象,记忆中模糊的画面在张怀礼老人的描述下清晰而鲜活起来。
“荒野里的小动物早已迫不及待,我眼前不时有野兔的影子匆匆闪过。麻雀和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在低矮的梭梭柴和红柳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鸣叫着,它们正高兴地欢呼黎明的到来。苍鹰不断地从高空俯冲而下,是在寻找良机捕获草丛里的田鼠、兔子等幼小的动物,来进行新一天的早餐。”读到这里,午后的阳光穿过浓茶的袅袅热气照在书页上,我好像忽然回到了童年跟随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在荒野上抓野兔的时光。我总是跑不快,邻居家的大姐姐就安排我守在兔子窝旁边……这位大姐姐现在已经当奶奶了。
1966年的11月,刘克增、李连会接到特殊任务,要去玛纳斯河对岸的连队拷贝纪录片,过河时却不小心掉进了湍急而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最后是凭着坚定的信念爬上岸,完成了任务。因为这次特别经历,刘克增、李连会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支气管炎,终生未愈。可是他们无悔,他们的回忆里这样描述着:“电影队的同志已经高高地悬挂起一个白色的电影幕布,幕布的前面是一片铺满积雪的开阔场地。只见场地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搬着小板凳、不停地奔跑着的孩子们,他们就像一群小麻雀在那里飞来飞去。这是他们为父母观看电影提前跑来抢占最好的位置。”那些像小麻雀一样兴奋地跑来跑去的孩子里面,也有我。
铁姑娘王胜敏的坎坷经历则铺就了一条光荣之路。她义无反顾地奔赴自己的爱情让人钦佩,无奈另嫁、痛失爱女让人无比同情,可是她不怕苦不怕累,总是勇敢地往前冲。
孔祥琴、王胜敏等人的经历,让我想起我的妈妈。她们都是“戈壁母亲”,她们都有一张梳着齐耳短发或者辫子,拿着《毛主席语录》的黑白照片;她们都是白天劳动不输男劳动力,收工回家还能洗衣做饭;她们里里外外一生操劳,都那么宽容和善良,用默默付出教会我们爱与被爱。
李连会念念不忘一盘再也吃不到的素炒芹菜;
勇敢救火的英雄任彦在垂垂老矣之际,才结结巴巴对初恋说出埋藏了50年的纯真情感;
王毛大已经珍藏了一张发黄的《无锡日报》50多年,因为那张报纸记录了他们一代青年远赴新疆的历史;
……
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场无怨无悔的青春奔赴。
合上书页,我的“溯流而上”却并未抵达终点,我似乎触摸到了父辈足迹的温度——那深嵌在荒原沟壑中的,是山东故土的坚韧基因在戈壁滩上开出的花。他们用青春丈量荒凉,以血肉浇灌绿洲,将“故乡”的定义,永久地锚定在了玛纳斯河奔涌的方向。
如今,玛纳斯河依然流淌。我们既是这条河流的见证者,亦是它未来的守护者与歌者。玛纳斯河流向的地方,荒原已成沃土,而父辈们的精神血脉正通过这河水,通过我们的记忆与讲述,永恒地流向未来。
强烈推荐兵团儿女们一起读读这本书——《玛纳斯河流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