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俗世传奇与地域书写
- 外汇
- 1小时之前
0 - 8
转自:贵州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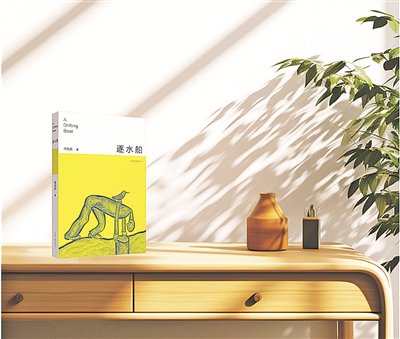 《逐水船》书封。 (资料图片)
《逐水船》书封。 (资料图片)
分享会现场。
 熊生庆近照。(资料图片)
熊生庆近照。(资料图片)■作家小传
故乡成故事
如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般,“在家乡这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掘出一口深井”的作家群中,多了一名贵州九〇后小说家熊生庆。简历显示,熊生庆是一九九四年生人,故乡六盘水市青林乡;现居省会贵阳,为贵阳市作协副主席。
熊生庆的故乡六盘水,小时候就有爷爷、父亲讲的故事相伴,“心里非常充实,生活得也很有底气”,长大后才发现好多听来的故事尤其是志怪故事,实则是《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书中故事的变体,换汤不换药。
熊生庆讲了父亲“人狗之间”的故事:“村里来了一条狗,那条狗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干翻了我们村里的6个人,其中4个还是非常强壮的男性。我爸受伤最重,差点丢了性命。他经过漫长的住院治疗,出院了。出院之后照样喝酒,在酒桌上他又开始聊年轻时的故事,各种战斗的战果。反正还是那句话,赢麻了。我妹妹脾气不太好,她挖苦我爸说,你连只狗都干不过,还好意思吹?我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那条狗,是会武功的。”
他还讲了堂叔“闯江湖”的故事:我有个堂叔,年纪并没有比我大几岁,在沿海城市的工地上做钢筋工。工地上太阳太大,被太阳晒了以后,一洗澡,身上的皮就开始一层一层地脱落。我和他聊在工地上做钢筋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每天干这个活,心里边已经烦得不行了。二〇一九年,熊生庆将堂叔的故事写成了小说《闯江湖》。“《闯江湖》给了我一种非常直观的生理上的冲击,或者说快感,一下子让我对小说这个文体,或者说这种表达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以后,他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琢磨小说这个事。一天深夜,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从这个时候开始先写个50万字,实在不行就写个100万字左右。通过大量的练习,看写小说这事到底成不成,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事。”熊生庆将这条动态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好在,熊生庆一直写下来了,将他们老家讲故事的“根气”、把爷爷和父亲讲故事的手艺,传承了下来。
写小说之前,熊生庆写过诗歌。二〇一九年,恰是他诗歌写作的第六个年头。“不再写诗”,是一件有寓意的事,表明他选择了小说的虚构之路。在此之前,他还走过一条“离乡进城”的现实之路。九岁时,他随父亲去县城参加表叔婚礼,这是第一次进城,乘坐的是中巴车,萌生了当中巴车司机的梦想。十三岁时,因病多次乘坐中巴车、面包车进城治病,见识了疾病的恐怖和城市的冷暖,少年的梦想由此淡却。再后来,他乘坐中巴车上高中、上大学,工作后有了自己的车。最终,熊生庆将这辆车开进了贵阳,将故乡写成了故事。在他的小说里,水城、荷城、杨柳街等家乡的地名反复出现。
“无论离开多久,只要有老家在,世界上的每一条路都通往故乡。”他在手机里,存着这条没发出去的信息。
贵州九〇后小说家熊生庆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逐水船》,收入作者近年来创作的十篇小说。小说的地理背景,大多以其故乡、“三线建设”工业城市六盘水为原型,这些作品此前已先后在《山花》《青年文学》《福建文学》《四川文学》《南风》等刊物发表,部分作品还被《中篇小说选刊》《思南文学选刊》《小说月报》选载。
结集成书出版以来,小说集《逐水船》先后入围“探照灯好书”6月原创小说书单、2025年7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等榜单,评语是:生猛而带几分锐气的语言与得宜的叙事节奏相伴,书写着发生在贵州工业小城和乡镇的故事,“苗刀”传人、下岗工人、离乡打工者、命运多舛的女子,这些穿梭登场的人物形形色色,他们多是经历生活、情感甚至生存的消磨后,依然有着坚韧、蓬勃的生命力,这些生命个体在作者笔下丰满而立体,共同构成有着地域特质与文学质感的俗世“传奇”。
近日,以“俗世传奇与地域书写”为主题的熊生庆新作《逐水船》分享会在贵阳孔学堂举行,与其人其书相关的作家、学者、编者、师友齐聚研讨。
作者自述:
故事的诞生与故事之外
“故事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分享会伊始,熊生庆以小说集《逐水船》的十个篇章为主线,分享了故事诞生的历程,以及故事之外的感悟。
小说集中,写于二〇一九年的《闯江湖》是最早成文的一篇。这篇以堂叔为原型的小说,给了作者直观的写作快感,顿时对小说这一文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他放弃了从事六年的诗歌创作,全身心琢磨小说。其大学老师、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思源说,《闯江湖》是熊生庆诸多小说中最先打动他的作品,“里面有着生活的粗糙感,蕴含着隐而不发的内在情感张力”。
西陵渡是六盘水牂牁镇的一个渡口。清朝中期,云贵总督修驿道、浚河道,原牂牁渡口改为官渡,并以其姓氏“西林觉罗”命名,简称“西林渡”,民国年间更名为西陵渡至今。在一次到访牂牁镇的经历中,作者了解到牂牁江景区的打造过程,包括当时已经被火烧掉的夜郎王宫,以及景点开发时最核心的水怪故事。“在相当一个时间段里,很多地方为了打造旅游景区,都会打造一些传说故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神农架野人、天池水怪等。牂牁江水怪也是类似故事的一个变体。”他认为这样的故事题材并不新鲜,但引人思考的是:打造经典的过程中,对当地一些特殊的人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他看来,所有小说故事的表达,最终一定落脚在人以及对人性的探究上,“这点对小说家而言是尝试,于我则是写作实践中的一次发现,以至于心旌摇荡,不能自已。我就是在那样一种状态下,把这篇小说写完”。
《西陵渡》里边有一个人物,四清的母亲,在《西陵渡》里这位母亲跟着一条卖小商品百货的货船走了。“我越琢磨,这个人物我越放不下。她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徘徊,时不时地跳出来。我就在想,她随着这条船漂走了以后,去了什么地方?这个女人后来又面临一些什么样的事?有什么样的经历?”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由头下,作者开始构思《逐水船》这一短篇。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跳脱出了《西陵渡》那一人物形象的原始影响,且有了新的身份、新的遭际、新的命运。“我第一次体验到了从一个小说生发到另外一个小说的过程。在写作的过程中,有一种非常切身的充实感。”熊生庆说。
接着,熊生庆在吴三桂征剿水西土司的历史背景下,将各种故事融合一炉,写出了《最后一刀》;而《气味》《晚照》两篇关注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歪酒客》则勾勒了滥办酒席者的心态。在这些篇章中,作者通过对人物及细节的观察,刻画出各种人物形象,描述了不同的生命状态。
“其实当一部作品完成之后,和作者的关系就没那么大了,它后续的传播、发表乃至于获奖,都只是一份意外的礼物,更重要的是能让读者从这些创作故事里,感受到文学的乐趣,引发一些对文学、地域及生命的思考。”熊生庆说。
论者他说:
小说最远可以抵达的地方
分享会上,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肖江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获得者魏思孝,以及河南文艺出版社传记与历史文化编辑部主任李建新,从创作、研究、出版等角度就《逐水船》进行交流探讨。
作为《逐水船》的“伯乐”,资深编辑李建新分享了作品发掘、选题立项、打磨出版的过程。为力保这部小说集的顺利立项,他不仅提前与出版社各个部门领导沟通,还特意制作了PPT,在选题会上解读作品亮点、转达文坛同仁的力荐,最终让《逐水船》得以成功立项。“到了稿件打磨阶段,文学作品的用词既要符合出版规范,又要守住作者的写作特色,尤其是那些鲜活的方言表达,删掉便失去了‘味道’,如何‘平衡’成了一个难题。”李建新称,为了作品呈现更好的效果,他和作者就稿件里的细节进行了大量沟通。他说,作为一个写作者,藏也藏不住,装也装不下,只要一直用扎实的作品说话,总有一天会被看到。
在作家肖江虹眼中,熊生庆的作品和年龄有一种惊人的成熟,“他有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安定的能力,可以把生活中的人物、事件等方方面面安排得妥妥贴贴。这便是他转写小说后,很快便能上手的原因”。具体而言,他认为熊生庆有着成为优秀小说家的三个特质:第一,对“故事”有清醒的认知,知道如何摆弄故事、表达故事。故事是传递内在情绪的载体,故事无法编造,只能发现。好作家不是“编造”故事,而是通过阅读、阅历和认知,从生活场景里“发现”本就存在的故事并表述出来。第二,往简单处做,拿掉冗长、多余的“无效叙事”,留下“有效叙事”。第三,擅长捕捉地域的“精神特质”,精神性和地域性在作品中很好地融合,让贵州的地域故事有了超越地域的文学张力。
“从写诗到转向小说,生庆一步步夯实基础,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对创作的初心与清醒,这份天赋加清醒,足以让他成为一位十分值得期待的小说家。”肖江虹说。
山东作家魏思孝说,熊生庆将自己的生活和写作达到了一种融合的状态,这种真实感让作品十分有力量,且不论身处何地从未放弃文学,也从未因文学理想陷入焦虑,这种对文学的热爱和坚持让人敬佩。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认为,如今城市环境大多趋同、地域特征不明显,不少小说都很难称为“地域书写”,但熊生庆的小说多围绕他的家乡六盘水,能让人感受到他扎根于自己出生成长三十余年的土地。“熊生庆不满足于对现实的表层记录,用虚构完善出一个艺术化的‘水城’‘荷城’,即便现实中有水城的地理、经济资料,他的小说能以虚构让这个地域世界更丰满,这是作品带给读者的重要价值。”徐强教授引用了作者在自序中“讲故事是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这一观点,认为作者的小说不仅故事情节发展合乎人物逻辑,且融入了丰富的地域背景——比如饮食、工艺、生产、民俗等细节,这些细节让故事更真实可感,带来的阅读体验也很顺畅,没有晦涩感,阅读体验很好。基于此,徐强教授进一步将熊生庆的小说称之为“地志写作”。
聚焦于小说集本身,徐强认为,作者善用短句,小说节奏感强,语言能力十分突出,在情感、伦理层面处理很稳妥,人物与情节也极少走向极端,“这种含蓄、节制的表达与人物间的和解,不仅蕴含着作者的人生观和生活哲学,也体现了他对世界及生命的独特思考。”此外,熊生庆的小说聚焦小人物,用“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以一个具体场景折射大时代的变迁与人心的变化,由此可见作者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及与当下表达的融合。
交流互动环节,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思源、贵阳作协主席王剑平先后发言。“今天的主题是‘俗世传奇与地域书写’,其实这世间哪有什么传奇?所谓的‘传奇’,不过都是生活本身——生活里有太多人、太多事、太多细节没被看见而已。而‘有心人’,也就是有情感、有温度、有人性关怀的人,会用敏感的视角捕捉到这些不为人知的生活侧面,并将其呈现出来。”张思源说。在他看来,熊生庆是一名“有心人”。
“以前写小说,多数人通常都是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但实际创作时会发现,或许应该聚焦个体对生活的不同体会,用个性化的书写呈现差异,而当这种差异积累成经典时,最终会成为全人类共通的生活经验。”王剑平称,熊生庆的小说里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差异性,哪怕同样是写本土的乡村、小镇,他和贵州其他地域的作者风格也截然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种理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吴宇/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超 /图
(《探讨俗世传奇与地域书写》由贵阳日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